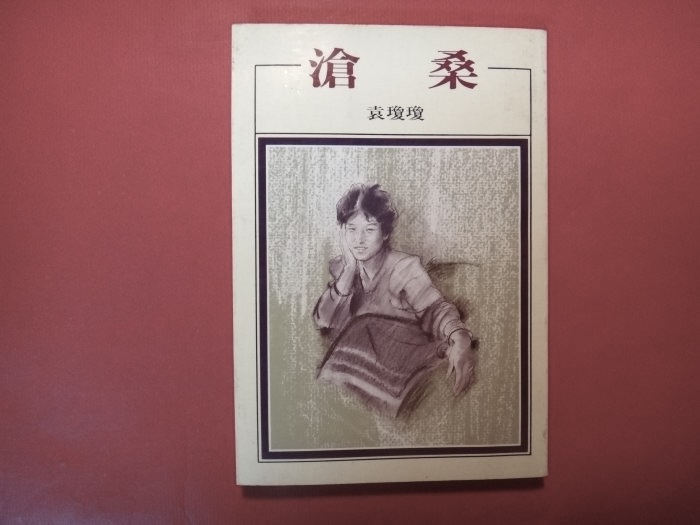
「滄桑」發生在一個歷史複雜的時代,成功地呈現了當時多數的社會現象;透過盧家和包家的角色,袁瓊瓊描繪的是一個男人參軍和留下女人相依為命的社群百態;像是不適應的楊青整天「哭哭啼啼」等場景(106頁)。而這種現象以及背後角色的情緒與價值觀,十分生動地穿越了歷史,跟現代讀者產生了共鳴。
在這種環境裡,孩子們很早熟。楊青拋棄了孩子跟游虎臣離開的時候,包家老大美蘭才八歲,爸爸受了打擊連續多天沒回家,是美蘭「帶著弟弟妹妹吃白水煮番薯藤,煮的藍不藍黑不黑」的,「姐弟三人吃得狼吞虎嚥,家裡連米都沒有」(122頁)。盧音是盧家的老大,境遇差不多也一樣,年齡不大就變成熟了,爸爸去世以後就成為了媽媽的左右手,而盧太太「大大小小的事情都找她商量」,使得盧太太認為她是被「心事壓得不長個子」(104頁)。滄桑裡唯一有些年輕少年味道的場景,只有一開始盧家四個姐妹在準備出門的那個畫面,「到底年代不一樣,作興化妝」(105頁);通過盧琴和盧瑟之間吵吵鬧鬧展現了年輕人的活力。而這個場景裡最揪心的,其實不是盧音不在意外表不愛打扮,而是對她來說,外表不能成為她經歷的焦點。盧音在故事裡,第一次出現就站在鏡子前,「踮了腳在看裙下的效果」(102頁);而她第一次發言,即是幫著盧太太擺平盧琴和盧瑟之間的衝突;只有盧音敏銳,知道盧樂在浴室裡準備著(103頁)。
沒有體驗過自在、無壓力的童年,並不代表一切都很糟糕!從故事一開始,就能看出來盧家姐妹跟媽媽感情不錯,四個姐妹穿衣服、化妝、準備好了就「擁著」盧太太出門(104頁)。五個人習慣性地一起熱鬧著並偶爾發怒。盧太太看來是很典型的刀子嘴豆腐心,說完了就忘了,「其實並不講究非要女兒們聽進去」(103頁);她也明顯是個容易擔心、會焦慮的媽媽,比方說,她憤怒的背後也擔心著女兒們未來如何,不趕緊嫁出去怎麼辦,「四個女兒,四樁心事」(103頁)。顯然讓盧太太很心疼罣心。
這跟故事最後的一個場景則正好相反,盧太太和楊青的對話有天壤之別。楊青跟孩子們的關係很糟糕, 唯獨大潭跟她還保持聯絡;美蘭拒絕跟她有來往,美茵只把她當成 「不相干的壞女人」 (第124頁),只叫了一聲「媽」(123頁),就很冷淡地把皮包遞給了她,完成任務就進屋了。相比起來,大潭和美茵叫盧太太「盧媽媽」都顯得更親切些。兩位母親跟孩子的關係之所以截然不同,原因也在於盧太太「雖然吃過苦,帶了孩子一塊熬過來了」(122-123頁),她們是一起把日子過得越來越好的;不像包家,是美蘭一直在經濟上支撐著一家子。包瑞行也承認,家裡的裝修與準備婚禮的費用,都是美蘭的「那一位」買的單(177頁)。
另外,故事裡三位主要的家長角色之間的反差也特別複雜。盧太太從一開始就顯出她是一位好面子的人,像是在家裡很自在,容易發怒,但到了結婚典禮上就變得小心翼翼,怕說錯話!紅包」顯得厚厚的」,盧太太才覺得「十分有面子」(113頁)。她也很擔心說出不該說的話,在跟包大潭聊天的時候,盧太太想問一些問題,卻「覺得不大好啓動口」,「人家家務事,也不便置評」,「盧太太頗有點好奇,但是從小輩口裡打聽到底不宜」(112頁)。
相比起來,大潭跟爸爸的性格很像,覺得沒什麼見不得人、說不出口的事;媽媽和姐姐時間的關係鬧僵了,他也不必隱藏。盧太太顯然向來中規中矩,腦子裡很清楚該做什麼和不該做什麼。她一開始「板板坐在位置上」,「悶坐了一陣子」(第113頁),才肯放下規矩,進屋子裡走一走。盧太太一直都是一個老實人,以前跟包瑞行是鄰居的時候也一樣,在丈夫去世以後,為了避免緋聞,在她和包瑞行的房子之間砌了道圍牆,因為「她不能不顧面子」(第116頁)。相比起來,包瑞行明明以前「不在乎」(第116頁),現在更無所謂地把緋聞當成了笑話,在新婚典禮上看到了盧太太的第一反應,就喊著「我的老相好來了」(第114頁)。也許她和包瑞行之間有過小曖昧,「接近浪漫的事件」(第117頁),但她打從骨子裡就沒有「風花雪月」的性格。也許這是因為當時社會對女人和男人的不同的價值觀的緣故。
同樣地,包瑞行也許也被社會價值觀困住了,無法表示自己情緒的波動,甚至跟「小葉」裡的劉智原相似。在最後小葉離開的時候,劉智原作為第一人稱敘述者,只承認「有一點點悲哀」(第35頁),就像盧太太在包瑞行面前提到了楊青的場景,是包瑞行在整個故事裡唯一一次對不愉快的事情有直接的反應,他很疏離地淡淡說道「來做什麼呢!十年沒見了,話都說不上來」(118頁)。這是一種自我保護嗎?還是社會的價值觀規定大男人不應該露出跟男女感情有關的過度傷心憤怒呢?包瑞行顯然因為太太出軌和離開受到了很大的打擊;連孩子都顧不了,「三個孩子自己在家,說是爸爸好幾天沒回來了」(122頁)。事實上,在盧先生過世以後,包瑞行幫忙照看盧家母女的行為,讀者能理解當事情發生在自己身上,並不是包瑞行不會養家,而是他的確做不到。這種有苦說不出的無奈,又跟「小葉」裡的劉智原很像。比如在用錢的事上,劉智原認為「男人用女人的錢,要能心安理得,那是孫子」(33頁);他也因此看不起自己。包瑞行很可能也有同樣的感受,看到了盧太太,他很快地自己提起了美蘭的「那一位」,修繕房子的四十萬也是「那一位」出的錢。他說得好像什麼事情都不上心似的,但也許他承認得太快了,好像故意把醜事說在前面,自己承認「知道有人要說壞話」,可是沒辦法,錢還是需要的(117頁)。好像故事裡 「自命一生風流」(115頁),顯得最自在的角色也會有說不出的苦與無奈。
最後,楊青則是一個心理很複雜的角色。勇於嘗試,但她一時的快活、自私和倔強傷害了她周圍所有的人。責任當然也不完全在她一個人身上,也許當時的婚姻真的不適合她,丈夫當兵的日子也的確辛苦。要是換個年代,也許她可以選擇離婚,事情也不一定會鬧得那麼荒唐。但事情的後果的確發生了,楊青卻覺得不甘心(難道包瑞行和他們的三個孩子不是更有資格感到不甘心嗎?)。不甘心的根源,主要是不服氣命運竟然是如此不可輓回,犯過的錯可能讓她後悔一輩子都回不到從前;「我只是不甘心怎麼這一錯,就回不來了呢……」(126頁)。只有在她叫出一聲「梅姐」並哭了起來(125頁),才表現出她真實的委屈和後悔,後悔耽誤了三個孩子的成長,使得他們吃了很多苦。
「滄桑」展現了許多能引起共鳴的社會現象和公認的價值觀——錯過的童年、刻板地好面子的言行舉止、男女關係的複雜程度和身為家長的責任等等。」滄桑」這篇短篇小說的寫實風格,也是它的可讀性的根本原由,因為那正是使得讀者覺得悶心的源頭!試問,在 「滄桑」裡,到底有誰過得幸福愉快呢?
© ICLP-NTU.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