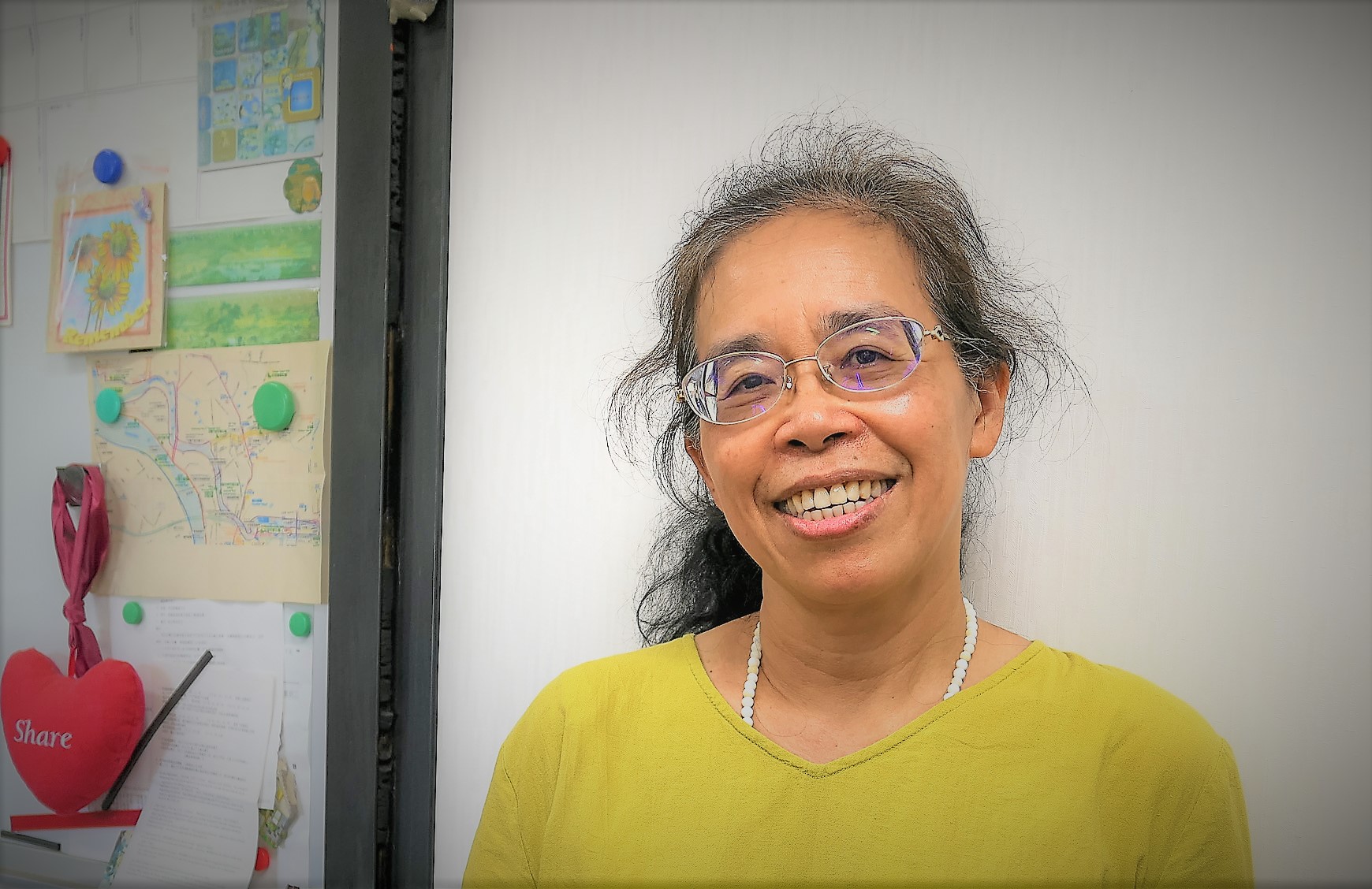
一、針對研讀第一手史料檔案之教學芻議
在華語教學中,研讀第一手史料檔案,是西方研究文史的學習者會接觸的課型。早期的西方漢學界的研究方式,一直是從閱讀理解著眼,原則上以英語研讀討論,並不重視中文的口語表達。目前則不再滿足於此,更思進一步培養學生自行研讀史料內容和中文的學術言談能力。再者,學術研究十分重視原創性,所以越來越多學習者選擇從第一手史料中進行研究,也是理所當然之事。根據ICLP的前身IUP第一任的丁愛博所長的訪答所說,當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教學的重點即是訓練口語表達能力;雖然當時的學生有時因為指導教授要求趕論文而忽視口語訓練,但主要的目標是第一年訓練口語,第二年才讓學生進行論文的專書學習。
目前ICLP的專書課型,是在這樣的傳承下展開的,而且更多元。為了符合以學習者為主體的教學宗旨,ICLP針對學生的研究規劃客製化的教學,而且十分多元。當然,所謂的客製化,是由學生提供專書的研讀素材,再由所方安排教師,協助學生解決語言方面的問題,這一點的認知非常重要!因為華語教師的專業是語言,並不要求如其指導教授般具備專精的學術知識,但需要通論、概論性的背景知識,以便順利地解讀相關史料的語言迷障。扼要地說,學習者的障礙是語言,不是欠缺豐富的學術知識,只要解決了理解文本的語言障礙,學生就可應用中文表達其所思所想,並從中發掘出具原創性的學術創見。
依我之見,在從事研讀第一手史料的教學的過程中,對師生而言,「教學相長」是彼此最大的收穫。我個人非常感謝有機會跟學生一起研讀第一手史料,等於是學生所提供的素材,讓我在上課前為了解讀文本而充分搜集相關資訊,運用各種方式排難解紛,也等於是自我充電,為我打開了新的視界。當然最大的喜悅,是學生在打破語言障礙後的喜悅和產生的新見解。當學生從第一手史料中照見了原創性的學術胚芽,將來會長出利益學術界新知和成就,那個成就不僅是個人的,也是整個學術界的。要進一步說明的是,本文是針對ICLP史料類型的「專書」的教學分享,不及於其他文學小說等學習研讀類型。身為華語教學的一名園丁,這是值得灌溉耕耘的一畝方田,所以我本著這樣的初衷跟大家分享一點我的教學過程點滴,就教於諸位,期盼能更利益學習者和教學者。
二、漢學研究歷程及教學需求簡述
關於文史方面的學術研究,東西方學術界都十分重視。東方學術界從中研院史語所的傳斯年所長(即前臺大校長,也是臺大傅鐘、傅園的紀念者)購入8000麻袋的明清檔案開始,著手整理這批影響深遠的第一手明清史料,由李光濤研究員挑選編輯,於1931年出齊《明清史料》甲編;其後於七○至八○年代成立明清史料工作室,從事整理與摘要等工作,1986年並與聯經出版社合作出版影印本《明清史料》,共計372冊。其後並進行數位化工程,進入國家型的數位典藏計畫,以利海內外學界使用。
西方學術界早期即注意到這類文史研究的教學需求,哈佛大學自1940年代起,即由費正清(John K. Fairbank)等漢學家針對清代史料(1644~1912AD)選輯,編纂成系列教材,主要有以下兩冊:
1.《清季史料入門》(1952)一書:主要以軍機處及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的檔案為主,讓學生熟悉宮中檔案的格式、官職層級及與西方接觸時的公文敘述等。
2.《清季史料2》(1986)一書:是以鍾人杰的社會事件始末為主,讓學生從中照見中央與地方及官吏與地方人士的觀點差異,並進一步分析當時中國社會的各層面課題。
上述兩冊清季史料的教材包括手寫文本,並輔以公文、歷代職官層級及所司之知識解說,不管是教學或是自行研讀,都發揮了極大的作用。
另外,研讀史料檔案首先需要面對的,是手寫稿的課題。由於早期的公文都是以書法謄寫,非目前的印刷文體,字體除正式公文的格式嚴格要求之外,真可以「姿態萬千」來形容。這樣將文字藝術化的書寫形式,連中文母語者都有一定難度,別遑論二語學習者了!因此,美國軍方早在1950年代就因情報單位所需,委由耶魯大學王方宇教授針對此一需求設計教材,編成《行草讀本》(1958)一書,總計涵蓋了300個行草字符,循序漸進地訓練學生辨識,為學習者奠定穩固的行草解讀根柢。根據編者說明,分析草書字符的根本困難,在於這些行草元素代表的多半不止一個正楷字,須取決於上下文,可見其辨識之難度。而該書貼心地提供了一種對照和練習方式,可以說是為華語教學界做出了極其重要的貢獻。
如上所言,研讀第一手史料的資料來源係由學生提供,其研究範疇極廣泛,甚且可說分流極細。根據我多年的教學統計,可以歸納出幾個特點:
1.出土簡牘形式;2.檔案收藏形式;3.公文應用形式;4.電報收發形式;5.合同簽約格式;6.表單條列格式;7.日記紀錄形式;8.書信往返形式;9.書法體式藝術形式。
就其時代之書寫形式可知,在印刷術發明到廣被使用之前,手寫的檔案就是所謂的「文抄公」產出的紙本史料;想要理解及掌握此類史料,就誠如編纂《清季史料》的費正清等所言,需要至少兩年的中文學習基礎,方能入手。入手之後再思如何鞏固學習者的自學和研究能力,進而發展成學術功夫。這就是本文所關注的課題,也就是如何有針對性的培養研究型的學習者帶得走的中文能力,奉獻其漢學研究於漢學界。
三、教學芻議
以現今研究型的學習者論,他們的中文能力已達流利精通級,不再只滿足於以英文解讀或二手資訊的研究模式,而是要求自身具備解讀相關史料的能力,希望從中照見歷史的絲絲縷縷。因此,學生的責任跟教師同等重要!簡言之,教師的責任是解決語言問題,學生則須在解除語言障礙之後,就自身的知識以中文呈現和分享其研究成果,以饗學術界,以至於世界。
想要成功的達成此一教學和學習目標,有針對性的教學是奏效的唯一法門,需要雙管齊下,師生通力合作來完成。而所謂的「芻議」,顧名思義指的是初步的建議,是我個人的經驗分享,並未經過實驗教學階段,期待能跟大家共同切磋。茲分述如下。
1. 建立文言文的基本功
依費正清先生在編纂《清季史料》(1952)的前言說明,文言文解讀能力極其重要!以中文語體而言,書面的正式語體都保留了文言文言簡意賅的特性,尤其是虛詞的用法;所以要研讀第一手史料檔案者,首要具備的是建立文言文的基本功。實際上,文言文的教學,等於是學第三種二語的學習,如何建立文言文的基本功呢?即是循序漸進地學習。如《文言文入門》(普大編)、《龍文墨影》(李英哲、鄧守信等編)、《進階文言文》或《古文觀止》等,最後就是進入學習者個人的研究專業領域一在深化厚植文言文的基本功之後,就能開展學習者自學、研究的本事。
2. 訓練辨認行草之手寫字體的功夫
研讀公文手寫檔案之際,需要具備漢字辨識和閱讀理解的能力才能掌握內容,順利解讀;因此辨識手寫字體等於是一個敲門磚,非充分掌握不可!面對這樣的學習需求,其中最需要訓練的,即是「行草」辨識理解的功夫,也就是《行草讀本》。教學時,可按照其各課的字符安排進行辨識,再輔以課後形符的英文說明,都有不錯的教學成效。其中最難突破的,是如何抒解學生因對手寫字形的恐懼。如中華語文研習所(TLI)TLI在《行草讀本》(王方宇,1958)的基礎上編了《行草漫談中國》、《行草書信》二書,提供更多的行草文本的接觸刺激,為學生建構行草的辨識意識。當然,拜網路資源豐富之賜,教學時,可以輔以網路或文人書畫之作品賞析,讓學生熟能生巧,也能從中培養學生的藝術美展之涵養。
3. 輔以公文格式及電報術語等常識
公文原本就是雙向溝通的管道和工具,能確切掌握上上下下關係的分野,方符合孔子所謂的「正名」關係。為了讓學習者更明了文本的遣詞用句,教學時,外國學習者更需要引導,大致可從幾個方面著手,如:1)提供正式公文格式、用語的認識框架(http://archive.ihp.sinica.edu.tw/mct/index.htm; 2)提供相關文獻參考書目資源(ex:〈近代公文書解讀-以近史所館藏外交、經濟檔案為例(初稿)〉(張力,2005);3)提供電報相關資訊簡介資料等,由於發報費用極貴,發展出以十二地支為月份代表字的系統,日期則用金代編修的《平水韻》的韻目代替等,更應為學生補充。
4. 善用網路學術資源之檢索系統
資訊科技的發展嘉惠學術研究的廣度、速度不知凡幾,身為華語教師的我們更是受惠良多!學習者的研究更需要這樣的挹注。然而網路的巨量資訊重複或訛傳者多,如何判讀也是一門學問。關於學術資源的整合工作,中研院一直是學術界的領頭羊,如網路資源之整合共享等,從1998年啟動至今,其人文社會的於2018年10月27日正式啟用「中央研究院數位人文研究平台」,讓台灣的人文資源分享及於全球,如能引導學習者善加運用,其研究的深度和廣度自然加成。誠如「中央研究院數位人文研究平台」簡介所言,該平台「乃根據人文研究的需求而打造」,旨在讓學習者「運用數位科技豐富研究材料、改善研究環境、促進人文研究」。我相信,對於不乏數位工具使用能力旳學習者而言,這也只是為他們開一扇窗,領進門之後,真的是「修行在個人」了。
5. 引導解讀文本之謄抄、摘要及提問能力
在所謂的「硬體」配備教學之外,最重要的,大概就是學習者「軟體」功能的擴充了,這也是我們在教學場域檢驗成效的一項重要指標。在教學過程中,除了硬體的操練引導之外,也需引導學生轉換和醞釀的的工法。在第一手史料導讀教學上,最重要的是引導學生理解文本;而理解的入門功夫,即是從辨識到理解以至於從中擷取研究精華。
具體而言,大概可以分成以下幾個步驟:1)要求學生預先謄抄文本;2)要求學生理解並摘敘大意;3)要求學生從中提出重要問題。華語教學教的是語言,至於知識的咀嚼、深化和回饋,則是摒除語言障礙之後學習者所釀造的學術精華,這是所謂「教學相長」的過程中的美麗豐收,值得師生全力以赴。
6. 訓練學術性論文的寫作論述能力
凡是進入第一手史料或專書研讀的學習者,都是未來學術界的尖兵,是撰寫學術性文章,這就是最後階段的「佳釀」。當然要有一支能言善道的的筆,都不是一蹴可幾的,主要有幾項要點:1)大量閱讀相關學術篇章;2)學習學術篇章的論述框架;3)習寫閱讀的心得感想及報告;4)訓練挑毛病和科學的驗證精神;5)建構學術論述的邏輯思維的完整度;6)訓練學生掌握母語與中文論述的轉譯能力。
另一個比較值得探討的課題,在學術界略有成就者都認為不必自行翻譯,一來是因為西方學術界並不重視所謂的中文論文發表成就,二來是要是其學術成就高,自然有人轉譯代勞。但要是轉譯者錯譯了研究者的主要論述呢?再者,若是研究者自身的中文素養夠,西方學術界對其中文的論述功夫怎麼能等閒視之呢?
三、結論
在教語教學界,研讀第一手史料檔案的教學實屬小眾,本文所關注的,是所謂的「漢學」專業的華語教學領域,這些學習者在世界性的學術界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甚至是漢學研究的傳承者,值得我們一起來關注。當然,我要進一步強調的,華語教學的每個環節都是不可欠缺的一環,環環相扣,在每個階段,由師生共同挹注心力,才能更上層樓。這篇小小的教學實務分享,其實是綜合了ICLP擔任此類專書教學同仁的經驗撰成的,各位同仁大概可以從中照見你們分享的點滴,我從中獲益良多,在此一併致謝。期望身為華語教學的同仁,都能由此教學實務的抛磚引玉,齊心協力,共闢新徑。
※參考文獻
1.《檔案學詞典》 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4。
2.《清末民初文書讀解辭典》,山腰敏寬編。東京:汲古書院,1998。
3.《歷史文書》 裴燕生、何庄、李祚明、楊若荷編著。北京:中 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
4.〈近代公文書解讀-以近史所館藏外交、經濟檔案為例(初稿)〉張力 2005。
5.〈民國時期電報日期代用字考察〉 張福通 《浙江萬里學院學報》 2007。
6. 《CH’ING DOCUMENTS》An Introductory Syllabus John K. Fairbank 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s 1952。
7. 《INTRODUCTION TO CH’ING DOCUMENTS PART ONE READING DOCUMENTS:THE REBELLION OF CHUNG JEN-CHIEH》PHILIP A. KUHN and JOHN K. FAIRBANK
8.《行草讀本》 王方宇 1958。美國,耶魯大學。
© ICLP-NTU. ALL RIGHTS RESERVED.